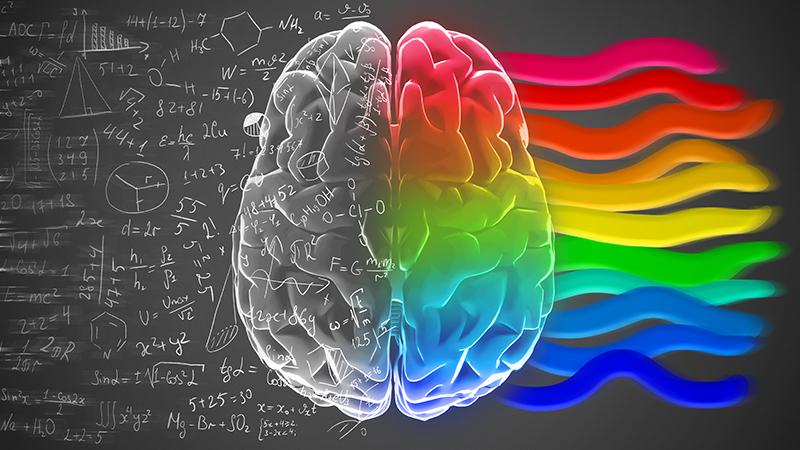
最近在多種報刊上,一再看到有學者提及張木生先生的新著《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我讀李零》。 在書中,作者反復揣摩了北京大學教授李零先生的著作,將他讀李文時覺得“憋得慌的地方”用直白的語言表達出來,讓大家看到李零關(guān)于國家命運以及文化立場的思考,以此為基提出,“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作者自言“逢左必右,逢右必左,超越左右”,對“歐洲中心論”、“中華老大論”、“中國模式”等命題都有所反思與批判。
該書于今年4月出版后,頗受關(guān)注。“最近幾個月里,思想界的討論都是圍繞這本書而起的。” 尤其是作者在書中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義”觀點,一時成為思想界爭論的焦點,劉源、吳思、楊帆、蕭功秦等都曾對此發(fā)言,進行論爭。甚至有論者認為,該書所凸顯的思潮走向很可能影響中國未來的改革走向,不可忽視,云云。
這些頗為高調(diào)的推崇,使筆者對該書產(chǎn)生了強烈的好奇心,但展讀不過數(shù)頁,卻大失所望。暫不論作者對當下中國社會問題的診斷是否準確,也不論其開出的“新民主主義觀”的藥方是否可行。僅就《改》的行文邏輯來說,就毛病多多:前后矛盾、以偏概全、浮泛空論等等舉不勝舉,再加上諸多枉顧常識的判斷,令人幾有不忍卒讀之感。現(xiàn)舉數(shù)例如下:
“在歐美,除了少數(shù)漢學家,其他各種學家都不了解中國”(第9頁)“另外有一個值得反省的歷史,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是怎么出現(xiàn)的?許多人都很關(guān)心,現(xiàn)有的書都是歐洲中心論的成說,觀察的正確與否,決定性的還是文化立場。”(第14頁)。“其實西方的現(xiàn)代民主制和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制度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人種不是那個人種,文明不是那個文明”(第145頁)“專制與民主都有相通性,都是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150頁)
這種不留余地、絕對性的說法,在邏輯上是犯了過度推斷、以偏概全的錯誤,只要一個反例,即可不攻而破。比如,美國經(jīng)濟學家弗里德曼并非是一個漢學家,但他的很多著作都對中國進行了研究,不少中國政要都接受過他的采訪,你能說他一點不了解中國嗎?歐美的漢學家、沒有上千,也有數(shù)百,作者都了解嗎?評判的標準又何在?再比如作者說現(xiàn)有關(guān)于資本主義起源的書都是歐洲中心論的成說,據(jù)筆者了解,《改》中引證的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即是典型的反歐洲中心論的著作。至于作者說西方的現(xiàn)代民主制和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制度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專制與民主都是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簡直就是枉顧常識,不值一駁了。
除了上述這般武斷、不留余地的說法之外,《改》書前后矛盾、相互抵觸之處也甚多。有時數(shù)行之間,甚至一句話之中,概念、觀點就南轅北轍。比如:“1949年后,海峽兩岸,判若兩界,新東西發(fā)現(xiàn)在大陸,研究也是大陸學者的貢獻大,大陸、臺灣新學的各派,成敗是非可探討,但它們的共同來源都是‘五四’。”(第47頁)既然作者認為大陸、臺灣新學的各派成敗是非可以討論,那么所謂的大陸學者研究貢獻更大這一結(jié)論又是從何得出?
再比如,作者認為“盡管資本主義自產(chǎn)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幾個世紀,但是到今天為止,西方學術(shù)界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什么是資本主義。”(第128頁)但就在同一頁,僅隔數(shù)行,作者又稱“其實,雖然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解釋過什么是資本主義,但不能否認馬克思已把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約定俗成”,再隔數(shù)行又認為“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仍然還是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概念”。馬克思是德國人,自然屬于西方學術(shù)界一份子。作者既然認為西方學術(shù)界還無人說清“什么是資本主義”,那么又怎能說不能否認馬克思已經(jīng)將“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約定俗成”了呢?既“約定俗成”,又“說不清”,令讀者無所適從。
上述錯誤較為明顯,讀者只要稍加留心即可發(fā)現(xiàn)。此外,書中還有大量較為隱晦的邏輯謬誤,值得分析。
“敵人是最好的老師,試想一下如果當年的中日甲午海戰(zhàn),勝利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國,中國也成了東亞的后搶者,二戰(zhàn)后期吃原子彈就不是日本人”(第148頁)這種論證手法,是典型的滑坡謬誤,作者不合理地使用了連串的因果關(guān)系,將“可能性”轉(zhuǎn)化為“必然性”,從而推出了想要的結(jié)論。因為即使中國打贏了甲午戰(zhàn)爭,也不一定就會成為東亞的后搶者。即使真的成為了后搶者,也不一定會吃原子彈。
再如“現(xiàn)在貶郭沫若抬錢穆,郭的學問,錢不可比,他們的不滿說白了是對郭的政治立場不滿”。(第39頁。)作者隱含的邏輯是,凡是認為錢穆學問比郭沫若強的,都是對郭的政治立場不滿。這是一種兩難推論法,將問題簡單化,只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
類似的還有“資本主義如同基因變異而產(chǎn)生的新物種,發(fā)展的極致就是今天的美國,不占盡全世界的便宜就難受,占盡全世界的便宜就更難受”。(第59頁)等等。再如“美國人的人權(quán)觀念是雙重標準。美國人在‘9.11’之前最反對見義勇為,對內(nèi)特別仁慈,對外特別野蠻,上層特別高雅,下層特別愚昧,對內(nèi)看似很文明,對外是變著方殺人”(第21頁)內(nèi)是誰?外是誰?上層是什么上層,下層是什么下層,作者沒有給出一個起碼的標準,浮泛空論,就好像“上面有多高”一樣,都是無意義,沒有憑據(jù)的推理。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只是筆者從書中順手抽取的,是否斷章取義,吹毛求疵,讀者可自行驗證。除了其他諸如類比不當、循環(huán)論證的邏輯謬誤外,該書給筆者另一個最大的印象是在概念運用上的極度不嚴謹。書中屢次提到“現(xiàn)代化”“資本主義”“西方”“左派”“右派”等概念,但作者基本上沒有明確地交代它們的具體指稱,即使在具體語境之中,也常常一變再變。
從作者的行文看,雖然對這些概念的復雜程度有所意識,但在實際行文中卻明顯 “化繁就簡”了。比如作者一再批判的所謂“西方”,就值得細細考量,究竟是哪個西方?是美國、英國,還是德國、法國,甚至東歐、日本?我們常常籠統(tǒng)地將這些國家稱為西方,似乎他們是雌雄同體,不分你我。美國學者史華慈曾敏銳地意識到將“西方”當作一個清楚、明晰的已知量是異常可疑的。他說,“我認為,在對待西方與任何一個確定的非西方社會及文化的沖突問題上,我們必須同時盡可能深刻地把握雙方的特征。我們所涉及的并非是一個已知的和一個未知的變數(shù),而是兩個龐大的、變動不居的、疑竇叢生的人類實踐區(qū)域。” 這提醒我們在運用任何概念時,一定要注意到概念內(nèi)涵與外延的發(fā)展脈絡,萬萬不能削足適履,大而化之地拿來主義。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此書并非毫無價值。作者在書中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義”觀點就值得充分重視,目前思想界對于該觀點的反應亦可證明。我無意在此陷入關(guān)于“回到新民主主義”、“歐洲中心論”、“中國模式”這樣的爭論之中,而是想以此書為例,著重指出一點:當下中國思想界在公共寫作、理性交流上存有很大問題。大概念、大判斷、大帽子滿天飛,觀點多于論證,感情多于事實,行文措辭缺乏基本的邏輯素養(yǎng)。這嚴重地影響到了當前思想界爭論的有效展開,既是作者智力上的極大浪費,也是對讀者智商的極大侮辱。套用這本書的書名,倘若我們不能“改造我們的邏輯修養(yǎng)”,討論再有價值的問題,恐怕都難以達到想要的初衷了。
殷海光曾經(jīng)說過:一本著作要能發(fā)揮它最大可能的效果,必須著者和讀者雙方密切合作。在著者這方面,他必須盡力之所及寫得清楚明白。……如果一本著作發(fā)生閱讀困難的問題,那么我認為首先需要檢討的是著者自己,不要動不動說讀者程度不夠。請問問你自己想清楚了沒有?寫清楚了沒有?
文章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書評增刊
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