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采夫/文 捧著作家馮杰的《閑逛蕩:東京開封府生活手冊》,不用掀開書皮兒就知道是河南人寫的,書頁墨香中摻著一點荊芥,還漂著一點油嗤啦。出生在廚師之鄉(xiāng)長垣的馮杰,跟開封一條黃河之隔,他帶著讀者趟過河,在《清明上河圖》里閑逛蕩一番。一千年過去了,《東京夢華錄》的遺民氣已經淡去,現(xiàn)代人馮杰回過頭去,從味覺出發(fā),重新探索汴梁的聲色和犬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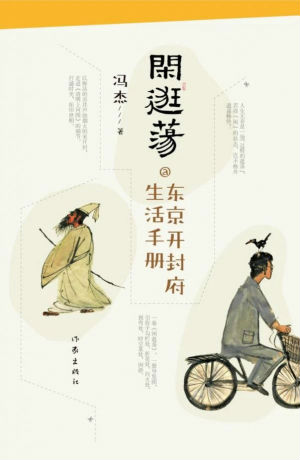
《閑逛蕩:東京開封府生活手冊》
馮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2023年11月
這是貨真價實的閑逛蕩,馮杰在《清明上河圖》里數(shù)人頭,他查出圖里一共有824個人物,95頭驢牛騾子馬。不過中原人的幽默藏不住,《戴院長吃豆腐》一篇寫的是戴宗去東京出差,被一盤麻婆豆腐麻翻在地,文末突然來了一句:“忽然聽牛老板高聲叫:快看,杞縣的大詩人王耀軍來了,當代詩壇神行太保。我今天要請他給我墻上題詩,中午上豆腐全宴。馮老師,你一定得來作陪!”
我頓時胖臉緋紅,果然親不親家鄉(xiāng)人,馮老師這是把我植入進去了嗎,我本名就叫耀軍啊。不過謹慎起見,還是查了一下,到底那個杞人憂天的地方有沒有一個叫王耀軍的詩人。這一查不要緊,人家有百度百科,落榜老高中生,精神略有失常,浪游中州大地,收容如同吃飯,經常在墻上刷他的詩和嘉言,其中一面破墻刷:“中國六千年來四大名人:伏羲氏創(chuàng)天下,毛澤東打天下,鄧小平治天下,王耀軍游天下。”落款1994年寫于周口。
把悲劇當喜劇,把苦難當笑話
王耀軍是河南作家宿命式的趣味,發(fā)自本能的戲謔。這種與生俱來的中原味道,在河南作家以外很難發(fā)現(xiàn)。
作為一個文學門外漢,我看書的方式就是亂讀,跟著氣味走,越熟悉越共鳴,所以打小對河南作家情有獨鐘。中學時讀李凖的《黃河東流去》,描寫黃河發(fā)大水:
“怎么這么大灰氣?什么也看不清!”話音還沒落地,只見從東北方向,齊陡陡,一丈多高的黃河水頭,像墻一樣壓了下來。李麥還當是云彩,天亮眼尖,她看到幾個大麥垛漂在半空,就急忙大聲喊:“水!黃河水下來了!”
作為一個住在黃河邊,曾坐著木船橫渡黃河的孩子,看到我的口頭語“齊陡陡”入了書,看到黃河之水天上來,心里咣當一下,就魘住了,癔癥了,用現(xiàn)在的話說叫“入坑了”。
讀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也是十幾歲。1960年代,李銅鐘為了不使鄉(xiāng)親們在大饑荒中餓死,帶領社員搶了糧庫5萬斤糧食,最后入獄而死。故事很悲慘,我卻只記住了里面的喜劇情節(jié),愛國衛(wèi)生運動評比大會上,“張雙喜謙卑地說‘俺李家寨衛(wèi)生運動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頭。可經過領導幫扶,向先進看齊,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驢兒總算養(yǎng)成了刷牙的習慣。……’真是語驚四座,使得外隊的所有匯報統(tǒng)統(tǒng)黯然失色了。”當時年紀太小,只顧著樂,后來才明白,把悲劇當喜劇寫,把苦難當笑話寫,寫出大悲劇、大苦難,寫出對政治忍不住的關懷,對腳下土地“恨之入骨”的愛,那是我們河南作家的獨門秘籍。在這方面,河南作家有某種共同的特質,而且很難被模仿。
今年是金庸100周年誕辰,我正在重讀他老人家的武俠小說,滿腦子都是武俠。于是惡搞了一下,把我喜歡的河南作家——當然是還在世的,編入我最喜歡的一個武俠組合——江南七怪。這純屬生拉硬拽,其實并不匹配,但為了好玩我就不要命了。陣容如下:飛天蝙蝠李佩甫、妙手書生劉震云、馬王神閻連科、南山樵子李洱、笑彌陀劉慶邦、鬧市俠隱馮杰、越女劍梁鴻。安排陣容的時候,有熱愛武俠的朋友提議,越女劍也可以是寫《寶水》的喬葉,她是我們河南的寶貝疙瘩。
飛天蝙蝠年紀最大,武功也高,是帶頭大哥。當年《羊的門》一出,群雄束手,至今仍屬于獨孤九劍級別。妙手書生性格詼諧,喜歡講笑話,所以《一日三秋》里花二娘在延津聽了三千年笑話。馬王神有三只眼,能看穿世道,正如《受活》的狂想現(xiàn)實主義。南山樵子言必有中,切中要害,《應物兄》對知識分子的刻畫亦入骨入魂。笑彌陀為人謙和,擅長死磕,當年讀《神木》沖得我潸然淚下,而且劉慶邦有佛相,有慈悲心。鬧市俠隱街上閑逛,寫寫畫畫,傾吐著對《北中原》的土味情話。越女劍錦心繡口,一生要“出梁莊記”,卻又念叨著“中國在梁莊”。
這個陣容一擺,我就有了我們村的老娘們當街一站、兩手掐腰、腆胸迭肚的氣勢,走向世界不敢講,沖出亞洲問題不大。
河南作家文學地圖
在北京與河南老鄉(xiāng)吃飯的時候,總要互相問一下對方是豫南豫北,還是豫東豫西,然后有一番說辭,什么焦作人肯吃苦,信陽人能抱團,濮陽人愛享受,周口人膽子大,洛陽人長得好看,南陽人有文化,都能給你盤個三四五六。當然任何一個省都有這種傳統(tǒng)。
這個道理用在文學上也一樣成立。學者楊義有一個口號: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他在《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里寫道:“中國文學如《詩經》《楚辭》從源頭上就與地理結緣,這是一個古老的農耕社會帶根本意義的情結和模式,不講地理淵源是不能講到這些文學經典的根的。”

《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
楊義 | 著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
把文學地圖的研究方法轉換成讀書的方法,再去讀河南作家的作品,畫一幅河南文學地理草圖,應該也挺有意思。比如劉慶邦是周口沈丘縣人,屬于豫東,他寫的小說《神木》被改編成電影《盲井》,如果不了解他的“宦游地”——當過新密的煤礦工人,就難明白為什么能寫出《神木》,以及那么些煤礦題材小說。
李佩甫是許昌人,他在《羊的門》里寫自己的豫中平原:“踏上平原,你會聞到一股干干腥腥的氣息,稍稍過一會兒,你會發(fā)現(xiàn)這氣息偏甜,那甜里還含著一點澀,一點膩,一點點沙。”“這就是平原的氣息,平原的氣息是叫人慢慢醉的。春日里,那雨后新濕的鄉(xiāng)間土路上,那隱隱的酒氣里會泛出一股女性的肉味……腐酸里會散出一股男人下體的臭味。”許昌離漯河的南街村只有幾十里地,那可是中國最有名的村莊之一。如果李佩甫沒有好奇地看過南街村,如果《羊的門》里呼天成沒有受到王宏斌的神秘啟示,那我敢輸點啥。
梁鴻是南陽鄧州梁莊人,南陽和襄陽爭了一千多年諸葛亮,有學者考證,其實諸葛亮生活在鄧州,只不過鄧州人不愛爭,也不愛吭。梁鴻的人生,是那種在最貧瘠的環(huán)境里最堅韌地掙扎,把自己拔出泥沼的故事。她的前半生就是拼命出去,走出去的時候流著眼淚,后半生就是頻頻回去,回去的時候也流著眼淚。梁鴻和梁莊的關系,像地頭上的蒺藜一樣扎得疼,又像疙疤草一樣砍不斷。
閻連科是洛陽嵩縣人,從村莊出發(fā)到部隊,最終到大學教書。閻連科開玩笑說他們村是世界的中心,因為河南古代是中原的中心,他們嵩縣又是河南的中心(洛陽“處于天下之中”),他的村子荒誕又永恒,生了人不報戶口,死了人不注銷戶口,最富的人上億資產,最的窮人吃不起餃子。村里的男女談戀愛,女的不同意,男的潑了女的硫酸,但是女方不找警察,而是對男人說,要么娶了她,要么賠10萬塊錢。不管多么神魔,多么狂想現(xiàn)實主義,《受活》就是寫的他的村莊,不管《丁莊夢》多么灼痛,寫的也是對自己鄉(xiāng)親的感情。閻連科說,如果丟掉村莊,他就丟掉了一切。
李洱是濟源五龍口鎮(zhèn)五龍頭村人,屬于豫西,在古代是荒僻之地,《水滸傳》里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的地方,離李洱家也就幾十里地。李洱偏重寫知識分子,但寫鄉(xiāng)村也是高手,《石榴樹上結櫻桃》里的農村人,在河南作家里最具現(xiàn)代氣質,在其他人向后看的時候,他筆下的鄉(xiāng)村在向前看。
劉震云老家延津已經和高密、額爾古納河右岸一樣,成為一個文學地名,被寫進了中國文學地圖。延津、塔埔、黃河、渡口、傳教士,劉震云建構了一個延津文學王國。那里是黃河的災區(qū),北方的大饑荒場場不落。外國傳教士老詹去延津傳教,被從教堂趕到一個破廟,每天晚上都要給菩薩上香:“菩薩,保佑我再發(fā)展一個天主教教徒吧。”
劉震云跟延津開著玩笑。他在《故鄉(xiāng)相處流傳》里讓曹丞相路過延津,軍隊秋毫無犯,夜深人靜的時候除了捏捏腳,另一個愛好是玩婦女,要求比較寬松,說“生瓜蛋子有什么意思?”所以鄉(xiāng)親們很擁護他。有天曹丞相問:“豬蛋,我這生活是否有些特殊化?”豬蛋啐口唾沫答:“什么特殊,我們延津幾十萬人,連吃帶日,還管不起你一個!”玩笑歸玩笑,劉震云的小說人物,同樣一輩子在出延津和回延津之間糾纏,我們豫北話叫“嬲”。
馮杰家在長垣,有那么幾回曾屬于濮陽,是離我最近的河南作家。馮杰家離延津百十里地,都是豫北。劉震云不安分,馮杰安分。不管《北中原》《午夜異語》還是《閑逛蕩》,讀的時候我常發(fā)出兩聲感嘆,第一聲是謝謝他為我們北中原記錄了即將消失的習俗、童謠、笑話、傳說、鬼故事,正被年輕人淡忘的吃食,感謝他為平原上的豬馬牛羊猴兔、棉花、大豆、秦椒、核桃、鯉魚作傳,他是鬼魅仙妖的知心老哥;第二聲就是感嘆我的娘啊,幸虧馮杰老師心無旁騖,連個普通話都懶得講,否則我們這塊黃河沙土地拿什么留人。
文學的出走與留守
在《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里,楊義還寫:“文學地理學第一個問題是地域文化,第二個問題是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還有作家群體的匯合、形成和最后風流云散的集散地。”我們河南這江南七怪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從豫南、豫北、豫西、豫東各自的鄉(xiāng)村出發(fā),經過當兵、考學、轉干、分配、教書、當記者、考研、調動、考博,就像聽到了某種集結號,就像《十月圍城》里某個奇怪的目標,最后落腳在鄭州和北京兩個地方。在大學里、協(xié)會里謀生,在大城市窩蜷下來,然后一趟趟地回老家。北京和老家,都成了并非久居之地的“梁園”,把嘆息和孤獨感撒了一路。他們的人生軌跡,一半是出走,一半是留守。
我對劉震云小說中一個情節(jié)記憶深刻。老汪的女兒掉水缸里淹死了,老汪很傷心,他帶著家人離開延津,“他一直往西走,到了一個地方,感到傷心,再走。從延津到新鄉(xiāng),從新鄉(xiāng)到焦作,從焦作到洛陽,從洛陽到三門峽,還是傷心。三個月后,到了寶雞,突然心情開朗,不傷心了,便在寶雞落下腳。”
這個情節(jié)不僅屬于傷心的老汪,也是作家走出家鄉(xiāng)的某種隱喻。
作家的宦游和流放不獨指古代(流放文學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學類型),放在現(xiàn)當代作家身上一樣適用。李洱的《導師死了》《花腔》《應物兄》,和他的人生經歷有解不開的聯(lián)系,包括《石榴樹上結櫻桃》,仍然是走出鄉(xiāng)村的知識分子對鄉(xiāng)村命運的思考。梁鴻如果沒有走出梁莊,就不會有文學地圖上的梁莊。
梁鴻的學者式寫作,閻連科的世界性寫作,劉震云的哲學式寫作,李洱的知識分子式寫作,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流放文學。他們的肉身出走,而文學經過淬火之后回歸。像寇流蘭和伍子胥,寫起故鄉(xiāng)來,反手一刀并不留情,因體會得深沉,所以扎的都是腰眼。但感情也是藏不住的,這就是忍不住的關懷,是恨之入骨的愛。他們共同體現(xiàn)出一種經過改造后的中原情結。他們站在了中國文學地圖的腰眼上。而馮杰選擇了中國文人的寫作方式,用筆記式寫作,詩、書、畫、文一起,為中原畫像,打著一個幡兒,搖著鈴鐺招著魂兒,這是一種自覺的文學留守。
關于出走與留守,在古代和現(xiàn)代,在文學和社會,在鄉(xiāng)人和知識人,都是值得探究的話題。一篇小文,一點感想,想不了那么深,累得眼疼,只有停筆了。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