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黃紀蘇/文
庚子年(陰歷)五月二十日,京城某士紳在日記中素描了一幅火災遠景圖:
將午,忽正南有煙,黃色直起如烽火,路人皆曰:“此焚屈臣氏藥房也”,市肆無驚,若豫知其事者。午后煙不止且變黑色。是日南風,其直煙變而為橫,從南而北,聚而不散,如黑龍之舞空,掠大內(nèi)而過,北逾鼓樓,仿佛汽船之在海,度其勢不止屈臣氏一家矣。
這是晚清史上一場著名的大火,縱火者的初心只是一家西藥店,結(jié)果卻是商家一千八百多戶、房屋大小七千余間燒得干干凈凈,人員倒沒什么傷亡。那一帶店挨店鋪連鋪、橫梁立柱、門板窗幔、桌椅板凳都是易燃物,這樣的下場并不意外。意外的是,火是白天放的,燒了一天一夜,搶運財物不缺時間,可老板伙計們卻只剩得一卷賬本、兩袖清風。他們?nèi)笔裁茨兀?nbsp;
京城另一居民在日記中為我們記錄了大柵欄火場的近景實況:
義和團在老德記大藥房將火點起,令四鄰梵香叩首。及至延及旁處,團民不許撲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無虞,切勿自生慌亂。即至火勢大發(fā),不可挽救,縱火之團民已趁亂逃遁矣。是以各鋪戶搬移不及,束手待焚,僅將賬目搶護而已。當時若不聽團民愚弄,先將貨物搶挪,雖云劫數(shù)難逃,究可保留萬分之一也。
義和團可以不讓大家救火,但攔不了大家撤離——那么多家哪里攔得過來?大柵欄人之所以沒緊急搬遷,是因為他們相信義和團指哪兒燒哪兒、不及無辜的先進技術(shù)。即便是火勢蔓延開后,據(jù)其他史料記載,他們也沒認為義和團技法無靈,而是埋怨隔壁廣德樓的撲救干擾了神術(shù)的正常發(fā)揮。他們覺著自己是“良民”,不是教民,本該在火外而不在火里。

《義和團史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2年5月
平心說,大柵欄被燒并非必然。如果義和團不把縱火作為常規(guī)武器,改燒教堂為拆教堂,焚洋行為扒洋行,火不聽指揮刀聽指揮、鎬聽調(diào)遣,那么就有可能實現(xiàn)精準滅洋。問題是,因此而不在火里的大柵欄人乃至更大范圍的人,是否就在火外了呢?答案后來人早就知道了。可“市肆無驚”的當時人呢?
一
得先對“禍”做點分解。庚子之禍可以分為直接禍和間接禍。直接禍包括殺人放火,針對的是洋人、教民以及涉洋人群;間接禍是直接禍引起的連鎖反應,包括社會動亂、經(jīng)濟凋敝、聯(lián)軍報復、巨額賠款等等,牽涉就沒邊了。直接禍中的毛子金發(fā)碧眼好分辨,暫可不論。“二毛三毛”可都是龍的傳人,由于直隸甚至山東進京的義和團人地生疏,他們?nèi)绾沃勒l是誰呢?老德記賣的西藥以及眾多洋行掛的招牌倒是“三毛”的身份標記,師兄師弟逛街時就能發(fā)現(xiàn)。但藏在小胡同里的“二毛(教民)”要是沒群眾舉報是不容易找到的,這其中,你本來不是漢奸,但仇人或政敵非說你是的可能性就不容忽視了,而且時人的筆記日記中也確有反映,例如楊典誥的《庚子大事記》便記有:“編修劉可毅,既非在教之人,第平時喜談時務經(jīng)濟,竟被義和團民所戕害。不僅編修一人遭荼毒,以是而喪身者實凡有徒。”想必義和團不會搜索并研讀劉編修的文章,他之被難,很可能是莊親王領(lǐng)導的聯(lián)拳滅洋工作組與義和團聯(lián)合執(zhí)法的結(jié)果。另外,義和團說二毛子腦頂有十字,一般人看不見他們能看見。幾十年后康生也憑借類似的特異功能偵破了不少“敵特內(nèi)奸”。義和團還有一項甄別奸良的絕技,就是點燃一道符箓,煙若是直的,嫌犯即可回家和親人團圓;若是曲的,身子和腦袋就分家了。我在史料中讀到最冤也最不冤的,要屬一些女性教民,她們在街上見了義和團嚇得跪地求饒,義和團并不念其主動投案,“率被拉去斬之”。
面對朝自己腦門飛來的直接禍,毛子的反應雖有快慢之分——法國的主教樊國梁有教民幫接地氣,一上來就意識到大事不妙;而英國領(lǐng)事竇納樂更多依賴清廷的上諭詔書、總理衙門官員的說辭神色以及其他上層線人的小道消息,剛開始并不覺得形勢有多嚴重——后來都緊著調(diào)兵遣將、構(gòu)筑工事。二毛也多扶老攜幼涌入使館教堂。西城有位教民想到親友家躲躲,可哪家敢接那禍呀,他們后來艱難輾轉(zhuǎn)才逃到了西什庫的北堂。總之,他們對直接禍的反應,可能沒羚羊豹子那么敏捷,但都能把災難看成災難而不是地壇廟會或淄博燒烤。
間接禍不容易說卻最值得說。間接禍位于直接現(xiàn)實之外,因果相對復雜,考驗的是一個人甚至一個文化的理性推斷能力。理性推斷不需要腦子多聰明,但需要腦瓜別太熱,太熱就成了傻瓜,會被騙子像牲口一樣地吆喝,別說見了棺材,就是進了棺材還偷著樂呢。理性推斷還包括借助他人的經(jīng)驗,尤其是淬煉成常識的經(jīng)驗,同時明白經(jīng)驗常識也不總管用,迷信不得。再有,頭雖不能太熱,心卻不能太冷,要有同情心,能設(shè)身處地、換位思考。同情心既是一種情感能力,也是理性推斷的前提條件。一個人對別處別人的苦難如果一點感覺沒有,當輪到自己時他會做出正確的判斷和及時的反應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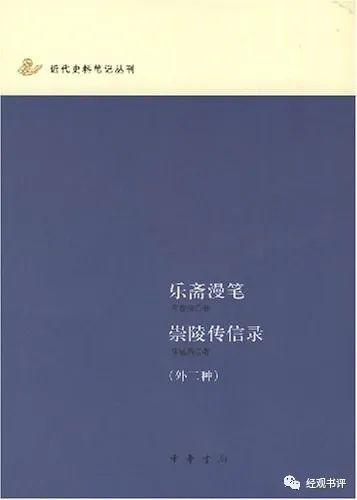
《樂齋漫筆;崇陵傳信錄(外二種)》
岑春煊 惲毓鼎 王照 高樹 /著
中華書局
2007年7月
大柵欄化作青煙的那一千八百家,商戶應占不小比例。對此我一直困惑:能把別人的錢挪到自己兜里的人,誰能蒙得了他們?我小時候換紀念章,兩個小紅章?lián)Q來換去換成了一個,而同伴卻一個倒成了倆,讓我一勞永逸地明白了自己腦子不夠用,后來誰下海我也不下。大柵欄的商人,怎么卻連“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常識都被義和團忽悠沒了?真不知他們的判斷力在中國商人中算高還是低的。上海的商人明顯高出一塊,1900年6月9日《新聞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論關(guān)心國事者惟商人》,說京津大亂的消息傳到滬上,“貨物不敢暢運,銀兩不敢劃兌,過客(商)不敢啟行”,商人都急成了熱鍋上螞蟻,天一亮就派伙計買報,半夜還到報館來打聽新動向。不久之前,上海的商紳一千多人聯(lián)名致電朝廷,懇請不要廢黜光緒,其政治站位令人刮目。
二
不過同在上海,官員跟商人又不一樣。據(jù)該文講,某巨商緊急求見當?shù)啬愁I(lǐng)導,巨商說得上氣不接下氣,領(lǐng)導“怡然藹然拈須對之”,末了來一句,國家興亡隨它去,操那心呢。巨商又求見了另一領(lǐng)導,領(lǐng)導說,我們這些外官跟京城的事沒啥關(guān)系。文中分析了官商差異的原因:商人的利益來自貿(mào)易,貿(mào)易江海相連,遠處也是近處;而官員的利益另有來處,北邊亂了他在南邊官照做、俸照領(lǐng)。該文感嘆道:事情只要不切己就不是事。其實,庚子的間接禍是否“切己”,官跟商的理解固然不同,官跟官也不完全一樣。東南互保的前提是東南疆臣的“大局意識”,即對間接禍的充分體認。其中的發(fā)起人兼聯(lián)絡(luò)員即是亦官亦商的盛宣懷,這應該不是巧合。
京中的官員對間接禍的態(tài)度也形形色色。這種復雜性在侍講學士鄆毓鼎一人身上都有體現(xiàn)。鄆毓鼎寫于庚子十年后的《崇陵傳信錄》很有名,有些專家會根據(jù)此書把鄆毓鼎劃入“剿拳和洋派”甚至“漢奸”。但從其當年的日記看,還真不盡然。以下順時針摘錄數(shù)則。
他五月初六日記到,“黃霾蔽天,日色無光,日有焚殺,大亂將至,心焉憂之。”
十二日,他請人用周易算了一卦,“其兆京城無恙”。
十五日其伯母七十六壽辰,傍晚他正和賓客一起聚餐,忽然傳來日本領(lǐng)館書記被甘軍殺害的消息,“大釁將起,同人相顧失色,狼狽散去,座客一空。”
十七日,“教民老幼婦稚,死無孑遺,尸橫路衢,火沖霄漢。京官來往者,不復常度,咸謀送眷出都。余義不容去,家累亦過重,聽之而已。”同日,他又找人算了一卦,算的結(jié)果是:“京城甚安,交小暑節(jié)即可漸定。”
二十五日,他帶著問題去了關(guān)帝廟,一問義和團是否真得到了神靈幫助;二問洋人能否殲滅;三問京城是安是危。得到的答復是一首詩加一首解詩,兩詩其實什么都沒說,但他卻讀出了“曉然圣意所在,拳民必可成事矣”。為了雙保險,他又用蓍草占了一遍,得到《周易》中一個擱哪兒都行的金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他解讀為:如果不將滅洋進行到底,國家就等著蒙羞吧。
第二天他在城外,“未刻,探事人出城,知十余國使館俱付一炬,洋人兵丁男女聚而殲之,無一生者。義和團奏凱而出。數(shù)十年積憤一旦而平,不禁距躍三百。”
之后,他的樂觀情緒隨戰(zhàn)場形勢每下愈況,六月二十六日他寫到,“一路拳民蟻聚,服飾詭異,神色狂悖,知禍不遠矣”。
鄆毓鼎對形勢的推斷,依據(jù)的是常識感、歷史經(jīng)驗、當前實踐(戰(zhàn)場形勢)、求神問卜幾項。他的“心焉憂之”,應來自以往哪次滅洋中國都賠得吐血的歷史經(jīng)驗(受神俠教育的民眾還真不一定了解這些),以及大亂之下玉石俱焚的常識。對于這樣的經(jīng)驗及常識,1900年初夏的鄆毓鼎也認也不認。之所以不認,是因為他相信鬼神,并通過占卜從鬼神那兒得知,義和團屬非常之人,有非常之術(shù)。也就是說,義和團既不歸常識常管轄,還可能廢了歷史經(jīng)驗。之所以也認,是因為義和團一敗再敗的當前實踐讓他“微悟此輩之不足恃也”。應該說,對于鄆毓鼎,當前的實踐是檢驗神術(shù)的最終標準。這種實踐標準當然比焚香拜表強,但它踩著現(xiàn)實的后腳跟兒,也只能是承認事實而不能推斷或預測事實。沒推斷預測也就沒提前量,而沒提前量等于撞上南墻才發(fā)現(xiàn)南墻。我閱讀這一時期的史料有得到個未必可靠的印象:在知識結(jié)構(gòu)和推斷力上,可以把的鄆毓鼎看作當時士大夫群體的平均數(shù)或中位數(shù)——也許略高一點。
 《袁昶庚子日記二種》
《袁昶庚子日記二種》
袁昶 /著
戴海斌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7月
和鄆毓鼎相比,大理寺卿袁昶可謂高瞻遠矚了。其《亂中日記殘稿》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寫到:“區(qū)區(qū)各駐使,勝之不武,屠此數(shù)人,彼族即不敢報復耶?”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祖謀在一道奏折中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東南督撫的態(tài)度也差不多,被緊急委以議和重任的兩廣總督李鴻章北上前給清廷發(fā)電,懇求千萬別再戕害外國使臣,否則他白發(fā)蒼蒼也只能白跑一趟。把幼兒老婦打殘打死不難,難的是人家的猛男找上門來怎么辦?這個常識不少動物都無師自通,可那些王公大臣卻一時都忘了,以為拿下西什庫、東交民巷就萬事大吉了呢。鄆毓鼎也是“距躍三百”之后好一陣才想起來。
三
當間接禍步步逼近、快質(zhì)變?yōu)橹苯拥湑r,不少官員或安排或率領(lǐng)家眷悄然離京。鄆毓鼎聽說詩人樊增祥也在流民圖中,特在日記里寫下“名士之可鄙如此”。樊增祥后來又躋身紅娘的大隊人馬,寫了著名的《后彩云曲》,將聯(lián)軍統(tǒng)帥瓦德西和妓女賽金花撮合在了一起。也有很多官員沒選擇離開,情況不一。如首先發(fā)現(xiàn)并收藏甲骨文的金石學大家王懿榮,被任命為京師團練大臣后長嘆一聲:老天這是讓我死在這兒啊!這位“看街老兵”籌措槍械彈藥求人求到遠在武漢的妹夫張之洞那里。北京城破,他與老妻、長媳先服毒后投井,和天門山約死群的模式相同。京城紳耆“仰藥以殉、引火自焚、投井而歿達一千九百九十八員名”,這些儒門書生確有讓人肅然起敬的一面。鄆毓鼎留下的原因比較復合:有他從掛簽蓍草那兒得到的定力:有出于職守紀律方面的考慮——他日記里對那非段常時期單位簽到點卯請假銷假等記之頗詳;也有遷大不易的苦衷——我印象中,在清人乃至民國人的日記書信中,交通費或盤纏是筆很大的開銷,像徐志摩那樣打飛滴穿梭于名媛之間簡直是特殊化到了逆天。
還有一些留京官員恐怕是沒想到“禍”也通“渦”,會像旋渦一樣把自己從禍邊旋到禍里,跟鬼子漢奸殊途同歸。他們或許是以為水再大也得從腳往上淹,腳上有腹,腹上有胸,自己屬中國頭部,且輪不到呢。這的確是社會的常軌,只是洪水確如野獸,先咬哪兒還真不一定。據(jù)當時人的書信,“東四牌樓頭條胡同起至王府井胡同止十余條胡同,滿漢官大宅門搶去不下二千家”。二千未必是確數(shù),也就隨口一估吧。當過帝師的孫家鼐沒能幸免,從家里逃出來連換的衣褲都來不及帶,顯然沒有思想準備,就不如現(xiàn)在有些官員,紀委同志來敲門,人家拉著行李箱正候著呢。與孫中堂地位相仿的徐相國也攤上了,其家被“搶得一空,屋亦燒去”。徐桐老先生是聯(lián)拳滅洋學派的首席專家,按常理真不應該。
那些綴滿朝珠花翎的官宦,無論哪種睡姿也夢不到自己有朝一日會被一些“”臨時農(nóng)轉(zhuǎn)非人員”拉下馬拽出轎跪在路邊,會被洋兵抓去抬尸體運渣土,一夜回到童子試發(fā)榜前。就連這個群體的“群主”及“群副”也是單衣薄褂倉猝“西狩”,全無“預案”。平日喝玉泉山特供山泉,這會兒途中口渴了,井里卻浮著人頭,只好拿根秫秸稈邊嚼邊嘬。夜晚寄居民房,太后凍得跟皇上背靠背苦捱到天明,自光緒親政以來,母子倆的心從來沒挨這么近過。雖然懷來縣接到通知,叫給副國級以上的領(lǐng)導預備滿漢全席,但規(guī)格歸規(guī)格,亂離中的接待水平最高也就是碗粥。吳縣長在逃空的民宅里廣搜博求,得到比天然雞蛋石還美妙的五個柴雞蛋,“親自”生火煮好呈上去,老佛爺吃仨給光緒留倆。

《庚子記事》
仲芳氏 楊典誥 華學瀾 高枬 等 /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輯
中華書局
1978年
再說義和團。京城有嚴格的城門啟閉制度,大官回城晚了,照樣吃閉門羹。但這是世間法,義和團隨到隨開,因為很多人,包括守城官兵及其上司都相信他們是上天派來的神兵,不同于一般勤王兵馬。他們開到北京后,“京城里九外七各城門,皇城各門,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門,均派義和團民駐守”,后來的西糾東糾都沒負責過這樣關(guān)鍵的崗位。殺袁昶、許景澄等大臣,由他們押送菜市口。除了滅洋,他們還挖出其他顛覆勢力如白蓮教。官方一直有人給義和團扣該教余孽的帽子,他們主動切割也能理解,問題是他們從“四鄉(xiāng)抄獲”的那些“白蓮教”就是一幫穿上龍袍冒充萬歲、戴上鳳冠冒充娘娘的戲劇愛好者,一群躺平卻還要叉腰的草民,這些人“臨刑時呼兒喚父,覓子尋妻”,慘不忍讀。說義和團接管了京城的公檢法似不為過,而且從捉人到砍頭,你說是一鍋煮也行,叫“一元化”也沒問題。當他們紅得發(fā)紫、舉著“興清滅洋”的大旗、揣著“清家”發(fā)的十萬兩紅包時,能料到不久被官兵拖著辮子一刀兩斷,鬼子在旁邊攝影存照么?
還有大眾,說多不忍,抄兩段時人的日記吧。其一在事變之初:“哄傳西什庫教堂大樓被焚,各處男婦老幼,人人鼓舞歡欣,隨聲附和,幌動街市。”其二在城破之日:“大街小巷逃走之人,男女老少擁塞道路,無分仕宦商民,俱拖泥帶水而行,嚎哭之聲慘不忍睹聞。”兩段的主語差不太多,狀態(tài)可差太多了。
還得說說洋人,他們是直接禍的受害者。那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棄孩病嬰義務當保姆的修女,何罪之有?據(jù)說山西某位修女被扔進火堆時說我救了不知多少中國孩子,你們怎么這樣對我呢?面對這樣的天問,有種回答聞著特別離譜:沒人去你家打你,是你上門找死的。照這邏輯,五一長假哪兒也別去了,路過人家門口就活該頭破血流。不過事情也確有另一面:1840年以來,列強沒少欺負中國,距庚子最近的日本割臺、德國占膠,都屬原汁原味的強盜行徑。庚子年中國官民針對洋人的那些做法,很難脫離這個大背景做孤立的理解。庚子被難的外國人士,固然是當日顢頇王大臣、愚昧師兄弟的直接受害者,又何嘗不是此前洋槍洋炮及不平等條約的間接受害者?后一點,不知道他們當時是否想到。不過據(jù)我瀏覽到的教會文件,事后他們還是有反思的。
還得說說教民,庚子年屬他們?yōu)碾y深重。此前所謂的“民教尋仇”其實并不對等:拋開是非曲直的錯綜參差不論,即便教民在日常爭訟中借助教會勢力對地方官吏施加了影響,非教民也多是賠幾桌席或幾臺戲,而義和團對教民則是非搶即燒、非燒即殺,感覺就像打乒乓球的遇上踢足球的。不過聯(lián)軍來了,一些教民如宣武門的安三兒又狐假虎威以搜捕義和團為名敲詐東家勒索西家,真讓人嘆息不置:還是只顧眼前,不想因果。你這一腳出去,踹倒的固然是別人,等轉(zhuǎn)一圈,飛來塊磚頭,不定誰家玻璃粉碎呢。
(作者為社會學家、劇作家,本文參考文獻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義和團史料》;中華書局:《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匯編》中文卷。)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