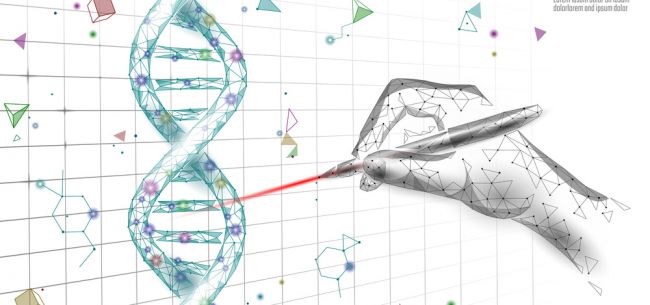
王陳/文
在歷史的很多階段,人類個體的某些不完美往往意味著命運的悲劇,有些人一出生就被剝奪了活下去的權(quán)利。
在這個層面上,與其說人類史是一部文明進(jìn)步史,不如說是一部歧視和殘害不完美同類的血淚史。更令人悲傷的是,這種歷史似乎從未中斷和發(fā)生本質(zhì)上的變化。
“阿波特泰山谷”
在古希臘,斯巴達(dá)城邦為了保證源源不斷的優(yōu)質(zhì)兵源,那些羸弱畸形的男嬰在經(jīng)過“貴族元老議事會”鑒定確認(rèn)后會被處死,并被扔進(jìn)西部邊境一個叫“阿波特泰”(Apothetae)的山谷里。因為城邦只會耗費資源養(yǎng)育那些身體結(jié)實健壯的男嬰,將他們塑造成勇敢善戰(zhàn)的“斯巴達(dá)勇士”。
在斯巴達(dá),撫養(yǎng)女孩所花費的資源并不比男孩少。湯姆·霍蘭在其著作《波斯戰(zhàn)火》一書中提到,女孩會被培養(yǎng)為未來的優(yōu)秀育種者,湯姆·霍蘭寫到:“未來母親的最佳標(biāo)準(zhǔn)就是容易生育,斯巴達(dá)人會通過皮膚的光澤和乳房的形狀來判斷這一點。斯巴達(dá)姑娘們以其身體的美麗而著稱,擁有長長的金發(fā)和優(yōu)雅的小腿——這為判斷道德是否高尚提供了現(xiàn)成的標(biāo)準(zhǔn)。”
而在中世紀(jì),歐洲人對于不完美者的典型歧視,則表現(xiàn)在疾病領(lǐng)域。整個中世紀(jì),醫(yī)學(xué)被神學(xué)和宗教裁判所掌控,社會對于麻風(fēng)病患者帶有普遍的歧視,麻風(fēng)病人被排斥、被禁閉,孤懸于大陸之外的海島上,麻風(fēng)病院是他們最后的歸宿。
精神病患者的待遇則不太一樣,法國哲學(xué)家、“后結(jié)構(gòu)主義”代表人物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在他那本名著《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狂史》中說,人們對于精神錯亂的看法,在公元1500年以后才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在中世紀(jì),瘋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來逛去并受到尊重,可到了后來,他們卻被當(dāng)作病人關(guān)進(jìn)瘋?cè)嗽海环N“被誤導(dǎo)的慈善”大行其道。
這種轉(zhuǎn)變表面上好像是對科學(xué)知識的一種開明的、人道的運用,可福柯卻認(rèn)為,實際上這是一種社會管制的陰險狡詐的新形式。所以,《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狂史》一書被認(rèn)為最終敲響了西方社會禁閉制度的喪鐘。
在納粹德國,“第三帝國”試圖保持雅利安人種種族基因純正,優(yōu)生學(xué)便成為政治工具,這種工具殘酷且無人性。借著防止種族退化的名義,帝國內(nèi)政部長威廉·弗里克宣布新政權(quán)將把公共開支花在那些種族可靠和健康的人身上,花在“下等且不合群的人、病人、智力低下的人、瘋子、殘疾人和罪犯”身上的錢不僅要減少,還要對他們施行“選擇與消滅”的殘酷政策。
為支持德國盟友,1933年7月26日,日本政府也出臺了措施,要求此后有遺傳性精神病或身體疾病的人不能再申請婚姻貸款。幾個月后,日本政府又出臺了一項新法,將禁令的范圍進(jìn)一步擴大。
1930年代前后,具有強烈歧視色彩的優(yōu)生學(xué)并非僅在納粹國家存在。1931年,美國優(yōu)生學(xué)家哈里·勞克林曾提出一項計劃,要在后半個世紀(jì)對1500萬出身劣等種族的美國人實施絕育。1936年,他還從海德堡大學(xué)拿到了榮譽博士學(xué)位。
現(xiàn)代的“阿波特泰”
今天,“斯巴達(dá)勇士”被稱為“超級士兵”,一些國家希望利用人類基因組技術(shù)改良他們的士兵和軍隊。這樣的新聞在全球互聯(lián)網(wǎng)上隨處可見,已不是什么機密。美國和英國的國防部門進(jìn)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和“超級士兵”項目,曾引發(fā)了人們對于潛在的軍事轉(zhuǎn)基因技術(shù)以及生物武器化的擔(dān)憂。新的基因編輯技術(shù)如果真正應(yīng)用到對現(xiàn)代士兵的改造上,好萊塢電影《X戰(zhàn)警》、《再造戰(zhàn)士》和《美國隊長》里的場景,將不再是科幻和虛擬的。
與斯巴達(dá)人相比,現(xiàn)代人在保證嬰兒出生時就避免畸形或者羸弱的技術(shù)能力已經(jīng)今非昔比。依靠基因篩查、基因編輯等現(xiàn)代生物技術(shù),人類離隨心所欲的“生育控制”越來越近。現(xiàn)代父母們不必再像斯巴達(dá)人那樣,忍受孩子出生后就可能被拋尸荒野的痛苦。
可當(dāng)我們回顧現(xiàn)代基因技術(shù)的發(fā)展歷程,以及將其與倫理一并考察時,一條“阿波特泰峽谷”仍然若隱若現(xiàn)地存在于現(xiàn)實之中。
人類的生物技術(shù)史并不悠久,其突飛猛進(jìn)也就一個多世紀(jì)的事情。雖然人類很早就意識到了遺傳現(xiàn)象的存在,但對于遺傳的本質(zhì)的認(rèn)識卻開始于19世紀(jì)中期,更準(zhǔn)確地說是查爾斯·羅伯特·達(dá)爾文創(chuàng)立進(jìn)化論之時。也是在達(dá)爾文的影響下,他的遠(yuǎn)房表弟、英國博物學(xué)家F.高爾頓才于1883年首創(chuàng)了優(yōu)生學(xué)這個概念。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則認(rèn)為,優(yōu)生學(xué)是懸在整個基因?qū)W之上的幽靈——它意味著,只專門生育有著優(yōu)選的遺傳特征的人類。
福山注意到,十九世紀(jì)末二十世紀(jì)初,國家支持的優(yōu)生學(xué)計劃曾經(jīng)得到了廣泛地支持,這些支持的人群除了右翼的激進(jìn)分子和社會達(dá)爾文主義者,還包括費邊社會主義者比阿特麗斯·韋伯和西德尼·韋伯夫婦(Beatriceand Sidney Webb)、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共產(chǎn)主義者霍爾丹(J.B.S.Haldane)、伯納爾(J.D.Bernal),甚至女性主義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瑪格麗特·桑格爾(Margaret Sanger)。美國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話曾給福山留下深刻的震撼:“我們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緒穩(wěn)定、富有同情心和聰明的人,我們不需要傻子、蠢貨、窮鬼和罪犯。”
進(jìn)化論對于19世紀(jì)西方傳統(tǒng)認(rèn)知的沖擊力之大,無異于一場“核爆”,但達(dá)爾文并未進(jìn)入遺傳學(xué)的深海區(qū)。真正揭示遺傳的秘密的第一人,是那個叫格里高利·孟德爾的神父,1854年,當(dāng)他在奧匈帝國圣托馬斯修道院后院種下一批豌豆后,遺傳的秘密第一次被人類揭開。但他的新發(fā)現(xiàn)在此后幾十年中并未得到重視,直到20世紀(jì),科學(xué)界才重新審視他的理論,大量生物科學(xué)家才有了進(jìn)一步的探索,以基因技術(shù)為核心的現(xiàn)代生物技術(shù),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有人說,人類基因技術(shù)的發(fā)展把亞當(dāng)和夏娃開除出了伊甸園,也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基督教的神學(xué)基礎(chǔ)。
一個更具標(biāo)志性的節(jié)點事件發(fā)生在2000年6月26日。當(dāng)天,參加人類基因組工程項目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的6國科學(xué)家共同宣布,人類基因組草圖的繪制工作完成。全世界為此歡呼,人類生命科學(xué)的一個新紀(jì)元即將到來。
但在基因技術(shù)為揭示生命本質(zhì)、人類進(jìn)化、生物遺傳以及人類疾病治療帶來巨大希望的時候,新一輪“技術(shù)至上主義”狂熱也隨之而來,克隆技術(shù)、基因篩選、基因編輯技術(shù)時常讓人們想起瑪麗·雪萊筆下那個人造怪物“弗蘭肯斯坦”,基因技術(shù)再次引發(fā)了人們對技術(shù)倫理問題的關(guān)注和討論。
現(xiàn)代基因技術(shù)的進(jìn)步程度,已經(jīng)超乎常人的想象。2000年,美國密歇根州西布魯姆菲爾德(West Bloomfield)的莎倫·薩里嫩(Sharon Saarinen)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女嬰阿蘭娜(Alana)。阿蘭娜的細(xì)胞核DNA來自母親莎倫和父親保羅,但她的線粒體DNA則來自另外一位女性。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今日簡史》的作者)注意到了這件事情,他認(rèn)為,從純技術(shù)的角度來看,阿蘭娜有三位親生父母。
一年后,美國政府因為安全和倫理問題禁止了這項技術(shù)。美國研究方還試圖與中國中山大學(xué)進(jìn)行合作開展此項研究,但在2003年10月,這項試驗在中國也被叫停。
2004年年初,英國紐卡斯?fàn)柎髮W(xué)的研究人員向英國人類受精與胚胎管理局提出申請,希望可以培育“三親胚胎”。次年9月,該局準(zhǔn)許紐卡斯?fàn)柎髮W(xué)進(jìn)行這項研究,許可期限為三年,但前提是不允許將胚胎真正移植進(jìn)子宮中,僅僅允許進(jìn)行研究。
雖然各國政府和生物倫理組織對這些新技術(shù)充滿了警惕,嚴(yán)格限定非治療性技術(shù)的研究范圍。但是,總有一些科技狂人不斷地在“阿波特泰山谷”上徘徊,難以抑制住突破技術(shù)禁區(qū)的沖動。
對此,美國著名的政治哲學(xué)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2001年擔(dān)任布什總統(tǒng)的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時,就開始思考人與技術(shù)、技術(shù)與自然的關(guān)系問題,并有機會去討論“技術(shù)進(jìn)步帶來的人性焦慮”。此前,他因為批評羅爾斯的《正義論》早得大名,并在哈佛大學(xué)開設(shè)通識課程“正義”(Justice),連續(xù)多年成為明星式的學(xué)術(shù)人物。
2007年,邁克爾·桑德爾出版了一本不到十萬字的通俗小冊子《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zhàn)》(以下簡稱《反對完美》),試圖給人類基因工程敲下“暫停鍵”,反對基因技術(shù)泛濫和應(yīng)用于非醫(yī)療領(lǐng)域,把生物技術(shù)限定在合理的技術(shù)應(yīng)用范圍。

《反對完美》
作者: [美國] 邁克爾·桑德爾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標(biāo)題: 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zhàn)
譯者: 黃慧慧
出版年: 2013-5
2013年年底,邁克爾·桑德爾到訪中國,他隨身攜帶了那本小冊子,與中國學(xué)者和媒體進(jìn)行了深入對話,進(jìn)一步表達(dá)他對東方哲學(xué)的熱愛以及對技術(shù)進(jìn)步的擔(dān)憂。
在與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的對話中,桑德爾說,他注意到一個非常大規(guī)模的人類基因測序項目正在中國深圳展開,這是更為龐大的世界基因測序工程的一部分。他在荷蘭導(dǎo)演拍攝的一個紀(jì)錄片中看到,年輕的中國科學(xué)家們雄心勃勃,希望能夠從基因上對人類進(jìn)行重塑,讓大家更聰明。
這顯然與桑德爾希望看到的場景不同。《反對完美》一書的核心觀點是反對基因技術(shù)應(yīng)用于人類改良,比如通過基因技術(shù)達(dá)到肌肉增強、記憶力增強、身高提升和性別選擇等目的。
在《反對完美》中,桑德爾對于基因技術(shù)濫用于改造人類憂心忡忡,書中探討了基因技術(shù)給人類帶來的倫理困境。桑德爾認(rèn)為,人類追求“完美后代”的沖動,曾造成了一場巨大的人道主義災(zāi)難(他指的是美國在20世紀(jì)初期掀起的優(yōu)生學(xué)運動并深刻影響了阿道夫·希特勒)。
在隨后的一場媒體采訪中,桑德爾說他并不反對廣義概念上的追求完美,他稱之為道德培養(yǎng)。讓他擔(dān)憂的,是當(dāng)下盛行的“科技可以制造完美”這一對完美的膚淺理解,尤其反對基因工程可以制造完美這一觀念。
桑德爾試圖告訴人們,隨便干預(yù)自然的人類技術(shù)是一種冒險行為,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完美”。在他看來,以基因技術(shù)為基礎(chǔ)的人類增強技術(shù)的應(yīng)用,會破壞自然的道德地位,弱化對人的尊重,且打破了善與權(quán)力的平衡,進(jìn)而帶來社會的不公平。
趙汀陽認(rèn)為,桑德爾的基本立場可以說就是希望人的神話在其極限處能夠停下來,不要去挑戰(zhàn)自然的容忍底線。
桑德爾是西方社群主義的典型代表,社群主義是他的技術(shù)觀的基礎(chǔ)之一。現(xiàn)代西方政治哲學(xué)雖然都在羅爾斯的《正義論》一書中找到起點,但是,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抗在1980年代后,成為西方現(xiàn)代政治哲學(xué)的主流敘事之一卻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與自由主義強調(diào)權(quán)利基礎(chǔ)不同,社群主義強調(diào)的基礎(chǔ)是“共同的善”,他們認(rèn)為,正義和權(quán)利不應(yīng)是抽象的和形式的,而應(yīng)當(dāng)是實質(zhì)的和有內(nèi)容的,即它們應(yīng)該建立在共同體之共同利益的基礎(chǔ)之上所以在對待技術(shù)進(jìn)步上,社群主義者總顯得保守和謹(jǐn)慎。
桑德爾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如果有人跟我說生物技術(shù)可以從根本上改造人類,我不同意。技術(shù)是工具,我們?nèi)绾问褂眉夹g(shù)這個問題,技術(shù)本身無法回答。判斷如何使用這些工具,我們需要人類自身的判斷力、推理力和公眾的討論。”他進(jìn)一步認(rèn)為,要掌握基因改良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即“我們必須面對在現(xiàn)代世界的見解中已大量遺失的問題——有關(guān)自然的道德地位,以及人類面對當(dāng)今世界的正確立場等問題。”
在尊重自然、反對技術(shù)泛濫這一點上,福山和桑德爾站在了同一戰(zhàn)壕里。2002年,當(dāng)福山寫作《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一書時,他也注意到,現(xiàn)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誕生人工嬰兒。他當(dāng)時已經(jīng)意識到,用基因技術(shù)改造人類的最大危機,就是它會讓人類失去人性。而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這些都會因為這項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而得到顛覆式的改變。
對此,福山說:“我們卻絲毫沒有意識到我們失去了多么有價值的東西。也許,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后人類歷史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但我們卻沒意識到分水嶺業(yè)已形成,因為我們再也看不見人性中最為根本的部分。”
在桑德爾那里,這些“人性中最為根本的部分”是謙卑、責(zé)任和團(tuán)結(jié),這是我們道德觀中的三大關(guān)鍵特征,而基因革命會侵蝕和改變?nèi)祟惖倪@些特征。
但過去十多年里,基因技術(shù)應(yīng)用的發(fā)展速度顯然超出了福山當(dāng)初的判斷,也沒有遵循桑德爾的“節(jié)制的合理性”。各國的生物技術(shù)專家們都希望盡快推動技術(shù)的應(yīng)用步伐,很多野心勃勃的科學(xué)家明里暗里試圖突破技術(shù)和倫理的禁區(qū)。
這常常令人無比沮喪。當(dāng)亞當(dāng)和夏娃被開除出伊甸園,當(dāng)技術(shù)至上主義也被涂抹上某些神學(xué)的色彩后,人類現(xiàn)有的監(jiān)管手段就更難跟上技術(shù)前進(jìn)的腳步,也很難有人能在技術(shù)和倫理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紅線。
誰知道,邊界在哪里呢?
當(dāng)然,我們也不能悲觀失望到無所作為。尤瓦爾·赫拉利在思考人類命運諸多大議題的時候,還是樂觀地認(rèn)為,在未來幾年或幾十年內(nèi),我們還有選擇。“只要努力,我們還是能了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模樣,但如果真要把握這個機會,最好從現(xiàn)在開始。”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