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行員的妻子》
作為一個小小的古玩商、一個歷史系學生、一個不務正業(yè)小說家,費瀅二十年如一日地晃膀子,處理著散落各地的事實碎片:
從地攤假貨到良渚最北線里下河地區(qū)的先民;從十三區(qū)賭場里印度人抵債的半顆珠子到法蘭西學院漢學所廢置的圖書卡片;從亞洲書店地窖里的伯希和木箱到戴克成的古玩店。
由于“研究目標”過于分散,導致博士論文無法完成,可費瀅總號稱自己是個“撿垃圾的人”,正在“收集世界的邊角料”。
且慢,此人晃的膀子,跟本雅明筆下的flaneur(漫游者)是一回事兒嗎?
為何她永遠在打支線劇情,永遠在撿垃圾,永遠畢不了業(yè)?
留學生回國之前互相托付的那只大同電鍋,和泰州光孝寺輾轉取回的文物有何異同?
造假古已有之,搞歷史、賣古玩、寫小說都要面臨共同的質問: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
……
而所有這一切,跟所謂的“文學”又有什么關系?
八月初,跳島FM主播于是邀請《天珠傳奇》作者費瀅,以及“世界莫名其妙物語”的主播見師,一起聊了聊這些內容。經跳島FM授權,理想國將本期文字精簡版整理如下,也歡迎大家點擊鏈接或移步小宇宙等播客平臺收聽完整節(jié)目。
晃膀子、flaneur和city walk有什么不一樣?
于是:小費老師的兩篇小說里面都有寫到“晃膀子”。我想知道這個詞的來歷是什么樣子的?
費瀅:就是之前在豆瓣上曾經跟網友討論說flaneur這個詞應該怎么樣去翻,然后我們覺得“浪蕩子”有點不太恰當,比如小說中李石德其實是比較衣著考究的人,有點dandy,《天珠傳奇》里就叫他們“蕩弟”。所以其實晃膀子也不算是flaneur,而是一種“街溜子”。
于是:那你覺得它和本雅明筆下的flaneur是同一種類型嗎?
費瀅:我覺得不是。因為本雅明有一個很強的歷史觀,他會有一種新舊時代的交替,因為新的東西出現太快,舊的東西消失太快,從而產生的一種斷裂感。他始終是一個觀察家,他看著這些東西是如何產生、如何消失的,這是本雅明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特點。我們這個時代雖然也有很多新的東西,但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并不“新”,除了一些高科技的東西。我覺得如果本雅明復活,可能也未必會覺得我們這個時代能像他的時代那樣給他那么大的沖擊。
像我們現在的晃膀子,有可能就是很多無所適從的年輕人,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比如說我,從二十歲到三十多歲,十幾年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我總得找一個活兒,但又不想進入朝九晚五的工作輪回,所以只能選擇打點零活兒。晃膀子有可能就是這種,有了一點錢,我就要走在大街上把它花了,花掉之后我又要在大街上尋覓,看看有什么東西可以撿的,有什么吃的可以吃一下,或者是有什么零活兒可以接一下,這樣的人。
見師:我覺得flaneur一般都是講的是在拱廊街,那個時候先有了購物廣場,就有人在里面溜達了,不然的話冬天就太冷了,走在大街上也沒有暖氣可以吹。除了flaneur以外,還有一些跟他類似的人,比如說賭博的、妓女。

《飛行員的妻子》
在本雅明看來,這幾個類型是很典型的,在以前那種歷史觀里,他們是一些不太存在的人。在他提出這種歷史觀之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剛才說的這些人,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什么他們的位置。那個時候除了本雅明以外,還有很多的人,比如說里爾克,或者波德萊爾這些人,他們提出“現代性”這個概念的時候,很多時候關注的都是這些不知道該在哪里的人。但我們現在講的這些晃膀子的人,更像是沒法進入體制的人,就沒有他那么強的斷裂感。
費瀅:我覺得唯一的共同之處就在于,這在現代社會的價值里可能都是一種偏向于譴責的行為。因為他不產出。
于是:所以是一個生存狀態(tài)上面的不同,我覺得像波德萊爾和本雅明的那個時代,基本上是在一個巨大的社會和文化轉型期,所以他們所關注的對象,都是像煤氣燈、博覽會、長毛絨玩具、電影這樣一些新興的事物。
但我覺得小費老師在小說中提到的這些人物,他們游蕩的時候,關注的對象并不是這些特別新的、作為社會現象的器物,而是一些老的東西,這個好像是他們之間的一個區(qū)別。但是反過來講,本雅明自己也是一邊搜羅老的東西,一邊觀察新的東西,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共同點。
說到逛來逛去,一定會講到現在爆紅的一個詞City Walk,你們覺得City Walk算不算晃膀子?
見師:以前我心目中的City Walk,就是在Airbnb 或者Tripadvisor報一個旅游團,是很常見的一種當地旅游活動;還有一種就是在城里邊帶你逛逛菜場,跟你說說這個地方有什么名勝古跡或名人,比如賽珍珠曾經在這里買過一條鯉魚;或者你可以參加做飯活動。總之在我心目中它是一種主題旅游。跟晃膀子相比,它是一個非常有結構的、有明確的目的、絕對不可能是一個純溜達的行為,不然的話你沒法掙錢,對吧?
費瀅:對,我也覺得它是一個消費活動。其實它是跟現在一些視頻 App很想做的“本地生活”緊密聯(lián)系的一種商業(yè)行為。把這個概念炒紅之后,就可以推薦各種路線,搭配所有消費場所的門票,做一個團體的報價。
于是:那與此相比,晃膀子的人去的是哪些地方?看的是什么?消費的是什么?
費瀅:其實晃膀子的人有一個一分錢都不花的本事。比如說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想寫一個和平里地區(qū)的生活,我整天在街上晃,那肯定是要先去麥當勞要熱水,因為北京是一個完全沒有地兒可以待的地方,街邊也沒有長椅,如果不在公園附近的話就很可憐,大商場里面也沒有可以坐下來的地方,除非你要去吃東西,所以你首先要去麥當勞里要熱水,然后你要規(guī)劃好沿途幾個可以提供熱水的地方,或者是沿途有什么樣的公廁,因為哪怕你坐在星巴克里面喝咖啡,還是要去它旁邊胡同里的公廁上廁所。所以你只要搞準這幾個地方就可以了,每天消費控制在五十塊以內就是勝利,最好是一分錢不花。
天氣比較好的話,就可以在地壇公園門口的長椅上睡覺,天氣不好的話,你一定得待在麥當勞。待在麥當勞的時候,你會見到很多人,因為一般像麥當勞、肯德基、漢堡王這樣的地方,會給快遞人員設立休息點,那時候你就可以跟他們聊天,你就會發(fā)現其實很多快遞員在等單的時候手上都在盤手串,然后小學生進來的時候手上也在盤手串。
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可以推薦給大家,就是漢庭酒店,所有華住會系統(tǒng)的酒店大堂都很歡迎你,還會給你酒店免費的礦泉水,你還可以看酒店大堂里的書。漢庭的人說,畢竟他們是一個平價酒店,只要上架一些比較貴的書,很有可能立刻就被客人順手牽羊給帶走了,所以他們就只能上一些很便宜的垃圾書,但我也看了大概四五十本,也就是說我豆瓣上標注的大部分書都是在漢庭看的。
見師:我要補充一下,我認識小費這么多年,她給我的建議一般都停留在這個范圍里。十幾年前在南京,她跟我講說南師大門口有哪些地方可以免費晃悠;后來到了巴黎,我們就琢磨說哪家店的咖啡最不難喝,然后又便宜,你在里面可以坐得比較久;在外面溜達的時候就是圖書館、大學門口的自動售貨機這種東西;還有就是去小公園嗦粉,小說里面也寫到了那個小公園,確實便宜,而且她去那里賭博確實能賺到錢。

《飛行員的妻子》
如果永遠選擇支線任務
于是:我當時就在想小費是有多愛賭才能把這一段寫得那么好。
費瀅:一開始主要是發(fā)現那兒有好吃的,你花幾歐元就能吃得很飽,而且能吃到很多肉,還有免費的飲料可以蹭一下,主要是越南速溶咖啡G7和晚上很差的Whisky。
后來發(fā)現了賭博這個事兒。我一開始還不太會賭,當時我也沒有居留,巴黎警察局對待我們這種沒有身份的人,“無紙人”,其實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因為我們需要大約凌晨六點鐘去警察局門口排隊去更新居留,每天只放五十來個號,我有一次六點鐘起來渾身貼滿了暖寶寶,在大約零下十度的露天中排三個半小時的隊,然后放到第五十二個號的時候,他說今天不放號了,就在我的前一個。我就貼著這一身的暖寶寶回去了,回去之后把暖寶寶撕下來睡了一覺,到第二天早上四點鐘,誒,這個暖寶寶為什么還是熱的?一看說這個新產品可以四十八個小時不間斷發(fā)熱,于是我又把這些東西貼在身上,又去排了一次隊。
為了這個身份的事情跑了很多次警察局,至少有四五次,每一次都這樣去排隊,弄得人非常沮喪。當時我也就半放棄了,就想說算了,我也不要居留了,我也不要身份了,反正我也可以去聽課,沒有問題,我就不跟你打交道了。

《新橋戀人》
于是:聽到現在我基本上能夠明白為什么你跟你小說中的人物都畢不了業(yè)。
見師:我覺得忙于賭博和吃飯其實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還有就是,寫論文這種東西,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你剔除這些邊角料的,你得找出一個主旋律,不光是得找出來,你還得相信,并且給你整個文章梳理出一個很精密的邏輯。因為什么所以什么得出了什么結論,它得有一個明確的主線。像小費這種生活方式,這種整天在外面撿垃圾的人,你讓她找出一個主線,并且相信這個主線,是很困難的,她整天在外面打一些支線,對吧?就像玩《巫師》,別人都在里面兢兢業(yè)業(yè)打怪,救自己的養(yǎng)女,把主線劇情打完,并且跟人談戀愛,結果她進去以后,從頭到尾就在那里打昆特牌,劇情沒有任何進展。
有的人就是喜歡支線劇情,你讓她去做主線其實是很困難的,我覺得這其實也是很大的一個原因,寫論文的思維方式和撿垃圾的思維方式是很不一樣的。
本雅明也是這樣,他會總結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但是他也沒有主線劇情。“拱廊街計劃”就是一個大型撿垃圾計劃,它沒有任何的主線,它的目的就是把大家的垃圾撿過來,然后也不加什么,就是整理一下堆在一起,以開頭字母排序,就結束了。
費瀅:就像你的論文大綱往往跟你搜集的材料完全不符合,一些所謂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現在很紅的approach ,是完全沒有辦法跟你的素材相匹配的。這就是為什么老師們總是說,你要先解決一個小問題,能把小問題解決就已經不錯了。確實是這樣的,我們只能去解釋這些細枝末節(jié)的東西。
見師:一方面人不能處理大的問題——這個事情本來就不太能成功,因為要處理大的問題,并且找出這么大的一個主線來,那真的就只能靠編造了;還有就是,和書里的人物一樣,費瀅也喜歡把檔案卡反過來,看它背面的內容,然后就完全被它帶偏了,就像游戲里上一個支線還沒做完,你就做下一個支線了,最后那些村民就只能站在原地等你回來。
“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
于是:所以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做大歷史跟寫小說其實是一個可以互補的行為。因為我看有一個采訪當中,小費也提到過,說小說當中提到的這些素材,其實就是在做學術研究的時候留下來的一些邊角料。
費瀅:還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做歷史的時候,每一條引用素材都必須講究出處,包括二手文獻你必須要指出。但是在寫小說的時候,就非常地自由,中間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是編的,它是一個很能給人快感的事情,就像你每天放學回來,你媽都要管你,然后突然有一天發(fā)現媽媽不在家的那種感覺。
還有一個細節(jié)很有意思,我研究珠子的時候去聽了本校一個老師的講座,他說在法國做論文,你使用的文物資料都必須是考古獲得,他們不接受盜挖的,包括市場上流通的一些非認證的物品。比如說,我們知道大部分的珠子都是印度河谷或者是東南亞生產的,一些珠子是在緬北盜挖的,他們在東南亞市場上買了很多這樣的珠子進行研究,每個國家的學術規(guī)范還是很不一樣,有些確實比較嚴格,因為他們會說:那你怎么能斷定這些東西就是真的呢?
我們會面臨很多次這樣的質問。無論你是去做歷史,還是做古玩,無論是物質的,還是文字的,一切的素材,他們都會問:那你怎么知道這是真的?或者那你怎么知道這是真事?
于是:證實和證偽這件事情在學術領域中會顯得非常地絕對和必要,但是在寫小說的時候,它其實反而增加了創(chuàng)作者的一種自由?
費瀅:其實寫小說的時候,這個這種質問是更多的,比如說“這個小說寫得不像真的”“這件事看起來不真”“ 像是一個假的故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責難。甚至還有那種要突出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但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他杜撰的,或者是有意用一些素材引導大家去那么認為的。小說其實也面臨著這樣的一個倫理問題,就是你怎么能讓故事真?小說中的真實,跟所謂歷史敘事中的真實,或者跟放在你面前的一個物質、一個考古證據所提供的真實,是不是同一種真實?
你是怎么開始寫小說的?其實就是在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才會想,我可以動筆試試看怎么去處理這個真或者假的問題,我當然沒有辦法去回答,但是我可以去處理它。
每個時代都在追尋一種已經失去的東西
于是:好像造假這件事也就是在當代才會變得非常夸張。我看《天珠傳奇》后面那一段講到他們用糖來做這個假珠子,真是嘆為觀止。

《殺死了一只羊》
費瀅:其實造假古已有之。你知道宋代的人仿造漢代的玉器,清代的人仿造宋代的玉器,采用的方法都是低溫油炸,那怎么樣去分辨?要看從古到今不同的低溫油炸的表現,也就是看低溫油炸上面會不會有其他的痕跡。比如說,宋代的低溫油炸我們叫作“提油”,它是為了仿造漢代玉璧上的沁色,氧化鐵離子進去以后的紅色,或者是水銀進去以后的黑色,用油炸的方式把它給炸進去。
那么現代的油炸和宋代的油炸又有什么樣的區(qū)別呢?就是宋代的溫度比較低,現代會心急一點,它的邊緣就會出現一些細細的線,線上面會有鋸齒般的痕跡,這就是現代的油炸制品。民國的油炸又有不同的風貌,它會把所有的玉都炸得非常紅,就像我們叫作“老土大紅”的一種宋代的沁色。所以就是每一個時代都在仿古,都在作假,都在追尋一種已經失去的東西。
包括《天珠傳奇》最后一章講到的用糖把珠子染成深色,其實就是古代印度河谷給所謂的紅玉髓,也就是紅瑪瑙染色的一種方式,因為紅瑪瑙有纏絲的結構,所以要想要造出那種深色的、質地比較純的瑪瑙,就必須采用染色工藝,糖就是他們一直都使用的材料之一,也是用加熱的方式把糖的顏色給煮進去。
文字中的游戲時空
于是:很多人在看小費的小說時,會有一種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個時代的錯覺,如果不是出現像手機、簽證、量子鑒定儀、自動投稿機這一類關鍵詞的話。所以我想問一下小費,你覺得小說家的語感可不可以不跟隨時代的主流變化?
費瀅:如果是從小說開始講,這種寫法其實來自于我跟豆瓣網友以及見師關于游戲設置的討論。因為游戲中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就是,它的時間進程跟真實生命的時間進程有的時候是不一致的,那么它怎么樣去標注時間?你打到不同的地圖才會進入不同的時間,它是一個地理性標志,放在寫故事里面,其實我并不需要去標示它到底是什么時間,我進入了不同的地理性標志,它自然就會昭示用什么樣的時間進程。
包括文中的語匯,其實也標示了它的時間。包括你在閱讀時的體感和文本是怎么樣去交替產生作用的,這個我也比較有興趣,所以我也有意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有文有白的語匯,包括現代的網絡用語,可能是我自認為先進但其實很古早、很土的網絡用語,去讓你覺得我是打到了一個不同的地圖上,這其實是游戲里面一種非常常見的設置。
還有我對所謂的因果關系的理解,產生自我們經常討論的一本經,叫作《梵網經》,它覺得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就像一張大網一樣。但你不要去想它是平面的,它其實可能會有數個空間,或者是數個時間、數個維度之間的關聯(lián),然后是它當下所在的位置、那個點決定了它被其他的一些東西影響,同時它也影響了許許多多非常遙遠的事物,它是共振的一個大網。其實就說明了這個東西是不可預言的,因為你無法計算出同時在振動的東西互相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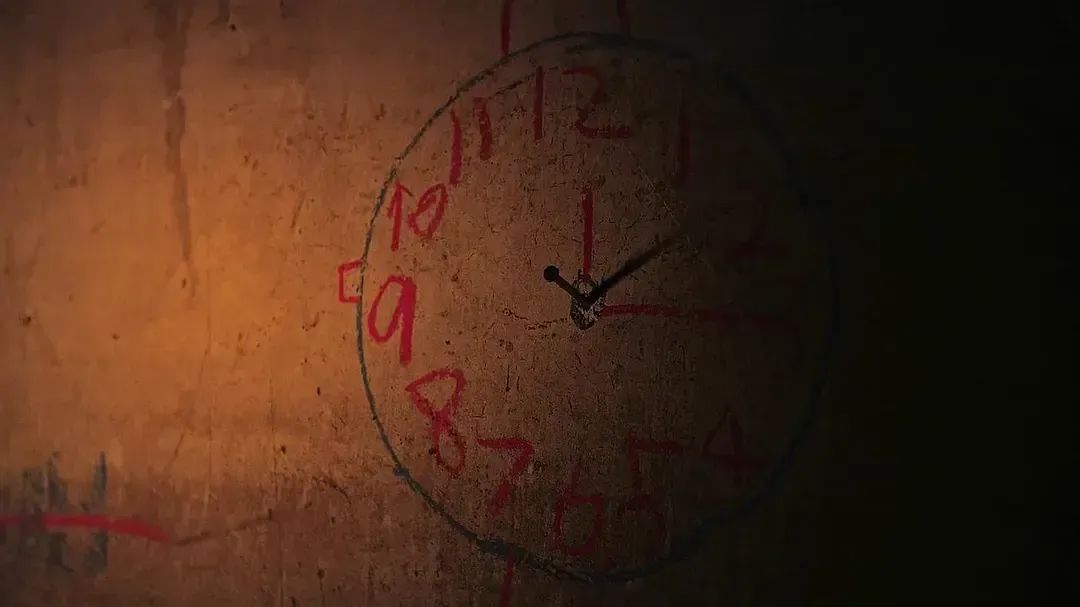
《路邊野餐》
見師:只是說游戲這個媒介可以讓我們更加身臨其境地體會到很多不同維度的時間在同時發(fā)生的這種可能性,因為游戲本身有一個游戲時間,還有一個敘事時間,然后你自己玩的時間,至少會有三層。而且它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就是一關打不過你會一直死,就不停地旋轉、循環(huán),過了這關以后它又變回線性時間,會有很多不同的結構在同一個故事里面發(fā)生。還有剛才說的時間是以地圖的形式呈現,它有很多種把時間擰成空間的東西,所以會比較有意思。
《梵網經》是說,有很多平行的解釋世上發(fā)生的不同事情之間聯(lián)系的辦法,但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哪一個辦法比另外一個辦法更對,因為我們畢竟就是一些撿珠子、穿珠子、撿垃圾的人,不一定能像歷史學家,他們會有一套標準,可以證明材料是真的,比如他們會認為閑魚上買的材料不是真的,但檔案館里的是真的。但是對于一個寫小說的人來說,不一定哪一個就比另外一個更真。
費瀅:還有一點我也很感興趣,你在游戲中死了以后,可以回到死的地方去撿回所有的東西,但是你的錢會丟,然后你又可以到村口去打牌贏錢或者裝備。比如我只打過《暗黑破壞神》,就是這么設置的。
原創(chuàng)文學究竟有沒有“原創(chuàng)性”
于是:剛才聽你們講,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觸,就是現在年輕一代創(chuàng)作者的敘事其實受到了很多層面的影響,但我覺得小費你找到了一個平臺,就是“物”的平臺,古玩也好,現實生活當中的物品也好,當你用敘事的手法去講述人跟物之間的關系時,你去闡釋它的真和假,或者去揣測它的來歷和將來時,一個故事自然而然就產生了。所以我覺得你的小說找到了一個特別好的起點,就是人跟物的關系。
費瀅: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因為我也只能寫我能寫的東西,然后這些東西恰好又是我比較熟悉的東西。我跟見師之前討論過一些問題,例如這樣的時間和空間的概念應該怎么樣在小說里面去構造,就是游戲里面的敘事策略的問題,還有游戲里面為什么會設置一個“撿垃圾的人”之類的。我之前對游戲以及網文非常有興趣,我非常想寫一個網文,或者寫一個地攤文學式的東西。
我先講一下地攤文學和網文的不同之處。地攤文學是以男女私密之事,以秘聞、丑聞為主的。然后網文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方式,它會有一個像數據庫一樣的東西,所有的梗、所有的套路都可以進入一個數據庫,它是在一個非常龐大的數據庫里面進行拼貼的一種游戲,區(qū)別只是我采取的是哪些素材罷了,網文一定要玩梗。
所以我當時想通過小說完成或者說實驗的是,很多東西它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原創(chuàng)性?因為在網文的時代去討論網文的原創(chuàng)性,其實是很沒有必要的事情。包括當代所謂的中國原創(chuàng)的嚴肅文學,它跟網文之間到底有什么界線?其實沒有界線。就算原創(chuàng)文學的作者已經進化到我們所說的“水準以上”的程度,也已經擁有了自己的語匯,但其實他的套路,他的各種方式,包括他關注的角度,其實都已經是被現代的讀者市場所定義的一種東西。包括作者的身份,包括我們今天錄制節(jié)目,通過整個一個營銷的流程,把這些東西送到讀者面前,它具有它的原創(chuàng)性嗎?其實我覺得未必。
所以我在小說里其實是有一些討論這樣的問題的意識,包括我在《行則渙》,特別是我的第二篇小說《反景》里面,用了很多很多前代文學或者當代的素材,很多文本其實都不能說是”典故”,就是“戲說”這樣一種文本類型。比如說魯迅寫的紹興戲、張愛玲寫的紹興戲,比如說唐魯孫,比如說用了大量的廢名。這對我來說就是所謂原創(chuàng)文學中的一種玩梗。為什么網文可以玩這樣的梗,嚴肅的原創(chuàng)文學就不能呢?但我發(fā)現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就是其實大家很多都識別不出,可能是我的讀者不夠多吧。
我覺得其實所有的文學都是一樣的,里面所有關于語言的游戲、形式、敘事策略,都是可以拿出來反復使用并且能夠被讀者認出、能夠會心一笑的,這應該也算是我的一種游戲設置。
物質世界中的流轉與關聯(lián)
見師:你要不要說一說《行則渙》這篇是怎么回事?
費瀅:其實《行則渙》這篇小說主要是探討的是一種對于“時間”和所謂“實存物品”,以及“虛構”的概念解析。它并不是要講一個什么樣的故事,而是通過物品之間的共同之處,讓它們自己去演說它們的意義。
其實《行則渙》里涉及太多的人和事。我寫的其實是家鄉(xiāng)附近一個小城市泰州發(fā)生的事情,書里的報恩寺其實是泰州的光孝寺,里面的南舟和尚其實是南亭和尚,當時是光孝寺的和尚去臺灣的時候,把大量的寺中文物托給了靜安寺,靜安寺的住持去臺灣之前又把這些文物托給了中國銀行,放在靜安寺的保險柜里。后來光孝寺在馬來西亞開會的時候碰到了趙樸初他們,趙樸初提出,我們要重新發(fā)揚宗教傳統(tǒng),光孝寺是否可以重建?重建光孝寺的時候,他們就申請再把保險柜的東西拿回來……其實書里寫了很多這樣的故事,物的流轉,不停地換手,但我覺得沒有辦法、也沒有必要把它說得那么明顯。
見師:費瀅寫的東西都有點搞笑,這種流轉就有點像留學生回國之前互相托付的那只大同電鍋:一開始它在一個臺灣學生手里,然后他要回國了,這個電鍋怎么辦?就可能托給一個大陸學生,然后過一段時間,可能又托給一個香港學生,最后這個臺灣學生又回來了,問,我的電鍋還在嗎?你能還給我嗎?
費瀅:所以說,一個物品能承載多少意義,其實跟它的流通、跟人的變遷有關,我就是想寫這樣的事情。就像大同電鍋,你說大同電鍋它本身有什么意義?

《路邊野餐》
文學的世界其實離我們很遠
于是:這三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一個“無紙人”的狀態(tài),在國內文壇還蠻少見到有人專門去寫的,放到更大的時代背景當中的話,你們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世界文學”“移民文學”這些標簽的?
費瀅:其實現在有很多的移民文學,作為當代外國文學中的一個門類,一般都是由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去寫他們那個族群的生活。之前移民文學還有很多的政治重量在上面,現在還會有一些“少數族裔”“女性”“后殖民”這樣的標簽在上面,所以移民文學跟我的處理還不一樣。
其實我這種叫作“流民文學”,確實沒多少人寫,因為華人去寫海外生活,一般都會抱有一些虛榮心,會有一點“高華”氣質,不會說我在國外混得很差。有海外背景的知識分子回到國內,其實他們在國外是拿到文憑的,可能也會擦桌子、洗盤子這種打工經歷,但是不至于像我一樣有那么長的時間沒有居留。
見師:你覺得你寫的是啥?
費瀅:我覺得我寫的就是一種狀態(tài)。
比如說,我馬上要寫一個新的小說,叫作《一九九〇年代的寫作愛好者》,這個小說的開頭其實還是在巴黎。我有一個朋友,有一天突然要請我吃飯,說,費瀅,你會不會處理法律文書?我說,什么法律文書?他說,我打拳的時候有一個師兄捅了人,所有跟我一起打拳的人都沒有居留,所以打拳的師父就問我們留學生能不能幫他處理法律文件。當時我還有身份呢,我才知道有一群所謂的“無紙人”在巴黎三區(qū)的一個教堂里,白天那個教堂做彌撒,晚上椅子挪開,所有人在那兒練太極拳。跟一個詠春師父練太極拳。為什么要練太極拳?因為他們要去參加法國的外籍軍團,這是他們能夠拿到居留的幾種途徑之一。
我想去調查,就說,那我也去打個拳。我爸就跟我講,你要去學拳,就去找我的一個朋友,他也在巴黎,原來是南京監(jiān)獄的一個警衛(wèi),他真的會打軍體拳,如果你想學的話,就去找他學。于是我又去找到這個打軍體拳的人,發(fā)現他都在跟我討論文學,他是一個一九九〇年代的寫作愛好者,但是跟他談論文學的時候,我也是沒有方向的,因為我當時特別年輕,還是一個本科生,他其實也沒有什么經驗,也沒有人去訴說,那我們在說的這種東西叫“文學”嗎?其實我不知道。我記得我跟他徹夜長談三天,每天都要到他家去吃飯,他和他當時的女朋友也盡可能地招待我,做了很多很多菜,他有很多對文學的幻想,包括他來巴黎其實也是為了更加接近文學。
我當時就有一個念頭,就是我們在討論的“文學”,它算是什么樣的一種“文學”?如果你把他所有的經歷都放在一起,把我后來真的沒有居留了又晃膀子了又賭博了這種東西放在一個更大的范圍里去討論,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流民文學。這個世界其實不屬于我們,文學的世界其實離我們很遠,哪怕是寫出小說,也離這個中心很遠,離我們所稱的那個“文學”的名字,以及文學的本質,離所有的東西都太遠太遠了。包括我現在寫的東西,其實也很遠。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